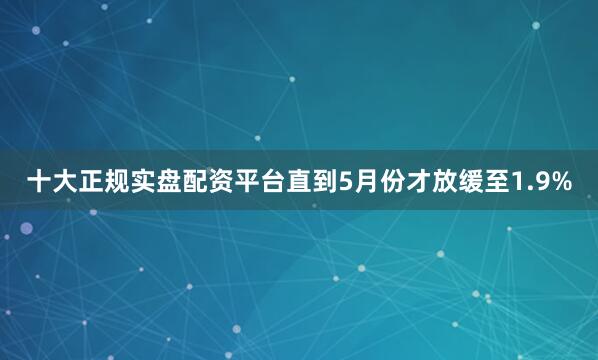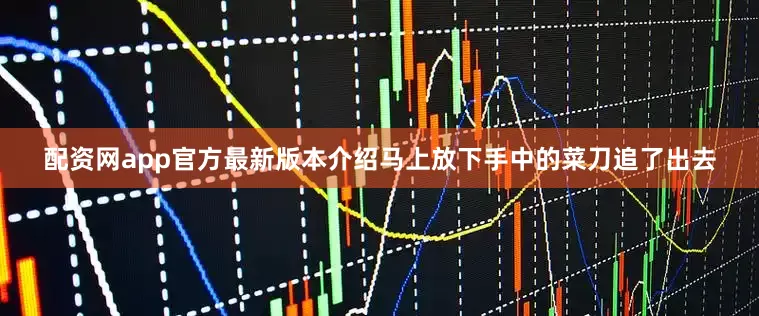
陈汝明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然而,在陕北延安的一个小山村里,他却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外甥。带着这个疑问,我通过北京的朋友王昌平老师联系上了陈汝明。原来,陈汝明曾是“知青”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他也曾插队到陕北农村,生活了多年。今天,陈汝明先生将和大家分享他那段珍贵的知青往事。
半个世纪过去了,陈汝明依旧清晰记得,1969年1月17日,他和一群同学在北京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家乡。那天寒风刺骨,陈汝明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(因为父亲是铁路工人),可依然冻得浑身发抖。当时,列车上不仅有他们学校的学生,还有其他学校的知青,大家一起坐上了开往陕西的列车。
列车到达铜川后,陈汝明和同伴们住了一晚,然后换乘解放牌卡车,继续向北行驶。他们经过宜君、甘泉,越过延安,历时四天三夜,终于在1月21日下午到达了延川县的刘家坪大队。陈汝明和另外十一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刘家坪大队的第二生产小队。六名女知青临时住进了队部的一间窑洞,六名男知青暂时住在刘队长家的一座空闲土窑里。
二队队部的窑洞不小,六名女知青住在大土炕上,刚好能安顿下。男知青的住宿条件差一些,刘队长家那间土窑虽然宽敞,但土炕太小,六个人挤在一起睡得很不舒服。最终,李小军和陈汝明只得睡在几个大木箱子和门板搭成的床铺上。
展开剩余78%那孔窑洞里有锅灶,刘队长为他们准备了锅碗瓢盆,还安排了一位叫刘玉荣的年轻婆姨来做饭。刘玉荣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妇女,大家都称她“玉荣姐”。村里的人有时喊她“玉荣嫂子”或者“根生嫂子”,但北京来的知青们并不了解她的背景。
刘家坪大队虽然靠近黄河,但土地贫瘠,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。好在知青们刚到时,国家提供了口粮,至少第一年的三餐还算有保障。
第二天,吃午饭时,突然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跑进了女知青们住的窑洞,拿起一个玉米面团子转身就跑。刘玉荣看到后,马上放下手中的菜刀追了出去,抢过男孩手里的团子,还狠狠地打了他两巴掌。男孩哭着坐在地上,陈汝明见状,赶紧跑过去,给他一个热乎乎的玉米面馍。男孩接过后,立刻跑出队部。刘玉荣回来时,不好意思地解释:“我家娃不懂事,给大家添麻烦了。”
随着时间的推移,知青们和刘玉荣渐渐熟悉了起来。刘玉荣透露,自己是个寡妇,丈夫李根生三年前在黄河口摆渡时不幸去世,年仅二十四岁。她有两个孩子,大的叫锁柱,五岁,二的叫二蛋,三岁。丈夫去世后,刘玉荣带着生病的婆婆和腿瘸的公公一起生活,家里生活困难,常常吃糠菜充饥。
春节的初一,知青们按照当地习俗,拜访了队长的父母和刘玉荣的公婆。当他们看到刘玉荣家只有黑乎乎的菜团子可吃时,大家都心生怜悯。刘玉荣说:“这两个团子是年前剩下的,我怕浪费。”从那天开始,知青们才真正理解了陕北农村的贫困,尤其是刘玉荣家过得如此艰难,连最基本的粮食都很难保障。
为了帮忙,知青们开始节省粮食,将余粮送给刘玉荣家。看到她家的孩子吃糠团子,大家心里非常难受。刘玉荣非常感动,她只能通过为知青们缝缝补补、关心生活来回报他们的帮助。
春耕时节,刘玉荣开始不再帮忙做饭了,转而和村民们一起出山劳动。她挑粪拉犁,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,知青们对她非常敬佩。特别是陈汝明,觉得自己比不上刘玉荣。
那年秋收时,刘玉荣一家分到的口粮最少,因为她的公公和婆婆劳动收入少。看着她家的困境,陈汝明提议将一片荒地开垦出来,种些洋芋和玉米,改善她家生活。虽然刘队长一开始有些犹豫,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
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知青们把荒地开垦成了梯田,并种上了玉米、红薯等作物。第一季收成不错,知青们不仅交了部分粮食给生产队,还把剩下的粮食和红薯送给了刘玉荣家。
由于这片土地的成功改造,其他生产队也开始模仿,刘家坪大队的农田建设有了显著进展。1971年,陈汝明被安排到刘家坪小学当民办教师。作为民办教师,虽然没有工资,但可以免去山地劳动,周末还可以休息,生活条件相对较好。
陈汝明任教后,决定让刘玉荣的两个孩子继续上学。他为两个孩子买了学习用品,特别照顾他们,确保他们不因家庭困难而失去学习的机会。经过劝说,刘玉荣最终同意让孩子们继续读书。
1977年,陈汝明考上了天津师范学院,成了刘家坪第一个通过高考离开的人。在离开前,刘玉荣为他做了羊肉饺子,两个孩子也回家为他送行。陈汝明离开时,刘玉荣激动地说:“姐一辈子都要感激你。”
此后,陈汝明和刘玉荣一家保持联系。1979年,他收到了李锁柱和李二才的来信,两个孩子分别考上了中专和高中。陈汝明为了鼓励他们,省吃俭用,把自己的生活费寄给了他们。
现在,李锁柱和李二才都在延安生活,过得很好。刘玉荣依然健康,和二儿子一起生活。每逢节假日,陈汝明都会收到外甥的问候和陕北特产。陈汝明也时常挂念着刘玉荣姐姐,关心她的健康。每次通话时,刘玉荣总是笑着提醒:“你可要注意保暖,别让腿疼再犯了。”
陈汝明常感慨:“有远方亲人的关心,让我感到幸福和快乐。”这份爱与牵挂,跨越了时空,让他深刻体会到亲情的珍贵与温暖。
发布于:天津市配资之家门户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公司平台倾向是取消一批文科类专业
- 下一篇:没有了